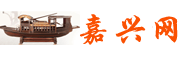阮婷玉
我喜欢读诗歌,隔几日就要读一些,就像是常日里总吃素菜,必定要来点荤菜来滋润一下日子;我也害怕读诗歌,怕到拿着诗集时忧虑的时间大过集中注意阅读的时间。我害怕它,我怕抓不住诗人那一缕稍纵即逝的感觉,我怕我曲解或自以为是地定义诗人的情感。诗人,是怎样一个桀骜的群体啊;诗歌,又是怎样一些精灵而稍纵即逝的文字啊!我如何能分毫不差又感同地成为第二个“诗人”呢?
当我试图去归纳《中的河流》每一辑的主题时,我的挫折感了我以上的“自知之明”存在的合。别想将自己的想法于诗歌之上,真的。《的河流》是活着的,你只能看,不能抓。正如它的题目一样,这本诗集里头活的东西宛若河流,“天塌下来,堵塞了它以外的所有河流,但是,它在流”。
这诗集于我,有三种共鸣:归宿、“静默如迷”的凝视和粗糙原生的想法。
无论我坐着、站着抑或是躺着,我常觉得脚下之地和身下之席乃至承载这两样东西的更广阔的空间,并非是我的归宿。我是奔波在远未到达的旅途吗?伊甸会问哲学层面上的问题:“我是谁?”“我来自哪里?”“我要到哪儿去?”这和他的身世有关。伊甸的祖上居住在浙江黄岩,父亲出生在杭州,他自己出生在海宁,却在桐乡农村的桑树林中长大。这种无根的漂流感,使他今天生活在嘉兴却依旧自觉是局外人。我不太敢问这样的哲学问题,但他诗中的寻觅感和途感总拍打着我的内心。
在《我从哪里来》一篇中,有这样的句子:“草根紧紧抓住了泥土……故乡紧紧抓住了风俗和沧桑……水紧紧抓住了河流……民谣紧紧抓住了村庄的秘密……冬天紧紧抓住了婚姻和荒凉……烛光紧紧抓住了整个乡村的寂寞……我是从这一切当中来的啊,这一切紧紧抓住了我。”丰富的意象,紧密相连的线条,但却读不到作者真正的归宿。“从这一切当中来”看似给了明确的答案,却不禁让人问是“这一切”中的哪个?在苍苍茫茫的中间,可辨得清来?可看得见去向?
而关于凝视,我觉得要是愿意在某物上放眼一定时间,便会得到某些奇异而汹涌如潮的东西。一些永不能再靠近一点的树,一些不能理解其光亮的星,一些刻在石柱上不能认识的名字,凝神看一眼便知它心了。至于看出的神秘、怪诞、空荡、深刻就都是你的了。
伊甸几近写尽了,这是我所理解的诗人式的衷情。他写得很随性,题目取得也很随意,譬如“看夜”、“看梦游人”、“看老人慢悠悠地散步”、“看雾”、“看烛火”、“看鬼”,我喜欢这样的漫际,这种凝视是不带目的的,你看到什么就收入囊中吧。
在《刻在柱子上的两个名字》里,伊甸这样写道:“这是一颗死去的树/它再不会生长/两个名字再不会生长/它们仿佛戴上了/灰尘在深深浅浅的刻痕中停留/又被风吹落下来/两个名字睡着了。”这不是看一眼的结果,而是凝视的结果—只有在凝视中,名字才会“睡着”。有那么多人我们不认识,我们各自前行,然后远远错开。原先便不识,又何惧相识又失却的永不可追回的遗憾?我们不能承载太多积累下来的情感转瞬化为陌的落差。伊甸大约也为凝视下的这两个名字,因为永不再相逢而悄悄地叹了口气。
诗人的想法很多时候是即时的、干裂的,这是我喜欢诗歌的原因。若说其他文学作品是打磨在前成型在后的话,那么诗歌应该是即时的成型在前,打磨是成型过程中自带的。诗人这些自然浑成的想法在慢慢聚集、交汇的过程中,天然地形成斟酌过的样子。
《一片皂荚树叶动了一下》是首有趣的诗。树叶动只是个简单的动作,因而也形成了最粗糙的想法:“一片皂荚树叶动了一下”。但恰是这样的原始、粗糙,在形成的过程中开始流动趣味和神圣。由“动了一下”,诗人想到它再也“不敢动”,又由不敢动,想到它大胆地“动了一下”,接着引发了风的“不敢动”,这一系列的动作由一个即时的想法全部引出,可谓妙趣横生。
有那么多的人,他们接触一切,却不抚摸一切。他们手忙脚乱,焦头烂额。他们不能思考,一思考就要怀疑。伊甸却含情脉脉,不紧不慢地写这一切。他一带着思索,心也是温热的。他写盛大或者沉坠,他说:“来吧来吧,都到我这里吧。”它们孤零零站界里,他不去打扰,只是默默凝视,像做一个古老庄严的仪式。
延伸内容: